關于幸福的討論很多。有人說,想要幸福就要“任性”一點,不要受困于別人的看法。但仔細想想,任性的人其實也沒有那么幸福,他們獲得的快樂持續時間很短。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呢?《被討厭的勇氣》
阿德勒說人際關系是煩惱的根源,但也是幸福之源。很多人相信幸福感是跟別人比較出來的。現代人的生活水平比幾十年前不知道好了多少倍,但是幸福感可沒提高多少。人們最在意的總是在人群中的相對位置。
跟別人比,比贏了的確能得到幸福感,但是這種幸福不自由。怎么解決這個問題?據我觀察,人們發明了兩個策略。
一個是假裝幸福。中國有句話叫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”,那我不和上面的人比,我專門跟不如我的人比,強行給自己灌輸幸福感。另一個辦法是消極幸福:我刻意地告訴自己,別跟人比!別跟人比!因為我害怕跟人比。
這些做法都是自欺欺人。本質上,你仍然認為幸福感是比出來的。
但其實比出來的幸福不叫幸福,它其實是不滿足,這種感覺是很短暫的。好不容易贏了一場,抬頭一看前面還有比你更厲害的人。年薪10萬的時候覺得如果年薪能達到20萬就會很幸福,到了20萬卻發現周圍好幾個人年薪50萬。
這樣的人生就如同參加登山比賽。你認為只有登頂了,才算是幸福的——登頂之前你只能算是在追求幸福的路上。這個游戲有兩個問題。
一個是,如果你始終沒有達成心中的大目標,那豈不是說一輩子都沒幸福過嗎?第二個是,就算登頂了,你還會發現有個更高的山頭在等著你。
每個人對幸福有自己的定義——但是你那個定義要想在邏輯上允許你獲得幸福,它最好是主動的,不能這么被動。
阿德勒提出的幸福,來自人際關系的高級狀態,叫做“共同體感覺”。
對此我是這么理解的。比如有個小村莊,生活條件很一般,村長的收入更一般,村里很多人不論是學歷還是收入都比村長高。但是,村里人大小事情都找村長,村長是全村人的主心骨。那請問,這個村長幸福嗎?
我們可以想見這個村長是非常幸福的——因為他知道自己的價值。他對這個村子有強烈的歸屬感,他是村里最重要的一員。
村里有個衛生所,主管的醫生學歷和收入也不高,醫術也挺一般,但是村里人生了病首先來找他。他能治療的就給治療了,村民花不了多少錢。治不了的,他會給病人介紹最合適的醫院。那你說這個醫生幸福嗎?
醫生知道自己并不像村長那樣被視為全村最重要的成員,但是他也會感到幸福。他是村民健康的第一道防線,他是村子不可或缺的一員。
那好,咱們再假設這個醫生有一位助手,助手只會做一些最簡單的工作,簡單到如果他不做,隨便找個手腳麻利的人也能做。今天晚上正好是助手值班,醫生不在。那請問這個助手幸福嗎?
我認為至少在值班的這一刻,這個助手也是幸福的。今晚他鎮守衛生所!誰有事兒,他是第一個要負責的人。村子需要他。
這樣的幸福不需要跟人比。其實咱們想想,所謂比出來的幸福,歸根結底比的無非是每個人的“價值”。但價值真的是可以比較的嗎?村長有村長的價值,醫生有醫生的價值,助手有助手的價值,這些價值是在不同的方向上,其實不能比較。
只要有一個理直氣壯的價值在那,你就是幸福的。
所以阿德勒提出,幸福就是你出于對社會的關心,作為共同體的一員,積極參與其中,找到歸屬感。幸福來自貢獻。
事實上,理解了阿德勒的哲學,如果我是那個衛生所里的助手,我不需要等到值班這一天就能感到幸福。我可以隨時感到幸福。
為什么像比爾·蓋茨、J.K.羅琳這類人,已經功成名就有花不完的錢,完全被社會認可,還要繼續工作呢?特別是比爾·蓋茨,一方面在非洲搞慈善,最近幾年還成了書評人,整天寫博客推薦書,他圖啥呢?
阿德勒的幸福定義可以解釋這種行為。J.K.羅琳幾乎不可能成為比J.K.羅琳更成功的作家,比爾·蓋茨的書評事業注定是沒有結果的。但他們需要保持對社會的貢獻感。
貢獻感能解釋很多幸福。比如有一位媽媽,每天全家人吃完飯,孩子玩游戲丈夫看電視,總是她一個人默默地收拾碗筷。你說這個媽媽會不會感到不公平呢?
如果她想的是,丈夫掙錢我不掙錢所以他有權不收拾,孩子們太小不會收拾,只好我收拾——就算她居然真的認同一家人還有地位差異,她也絕對不會感到幸福。
可是為什么千千萬萬個媽媽卻能心情愉快地收拾碗筷呢?因為她們知道那是在照顧家人。她是在為家庭這個共同體做出貢獻。
所以你承不承認,阿德勒這個定義其實挺好。而且請注意,幸福不是由具體貢獻的大小決定的,而是由“貢獻感”決定的。
算貢獻的大小,那是行為標準,中國話叫“論事不論心”,那樣的話一個因為疾病而失能的人還能有幸福嗎?他躺在病床上什么事兒都干不了,還需要別人整天照顧他,他豈不是會感到非常不幸福?
而“貢獻感”,則是存在標準,中國話叫“論心不論事”。在親人看來,這個人其實并不需要做什么,他的存在,就已經是一種貢獻。
在我看來最妙的一點,是阿德勒這個“貢獻感”,恰好符合康德對自由的要求。因為貢獻感是由你自己決定的。
貢獻感并不在于你的行為起到了什么結果,不是“如果……就……”。貢獻感是你認為自己做出了貢獻,你就做出了貢獻,你就立即獲得了幸福。
如果說貢獻難分大小的話,貢獻感根本就不需要分大小。你不需要非得達到一個客觀標準才能獲得貢獻感,從這個意義上講你不被任何外界的東西牽引。
貢獻感是非常可控的,你隨時可以單方面認為在這件事上你已經做到貢獻了——只要你能說服自己的內心。所以貢獻感也不是被內心的某個永遠不可滿足的欲念驅使。
事實上,阿德勒反對為共同體犧牲自己——別人的命是命,難道你的命就不是命嗎?你自己也不是工具!有貢獻感就可以了。
也許你做的這件事別人根本看不到,也許別人還誤解你,但是沒關系,你自己知道你做了貢獻。
當然我理解,這個貢獻感必須得真能說服自己才行,不要自欺。生活中有很多幫倒忙的事兒,有時候你以為你是在做貢獻,其實別人不需要你的貢獻,這種可不算貢獻感。
總而言之,以貢獻感為指引,你就既是自由的,也是幸福的。
如果你經常思考“什么是幸福”,阿德勒的這個“貢獻感”肯定不會讓你吃驚。各路哲人研究的幸福理論,最后都會得到類似的結論,可以說是殊途同歸。
說到貢獻感,我們必須知道你并非只屬于一個共同體!有些人對工作單位有很強的歸屬感,結果一旦被裁員、或者退休,就很難受了,就好像被共同體拋棄了一樣。
你要知道你除了屬于那個工作單位之外還屬于很多共同體:你屬于家庭、你屬于社會、你屬于國家、你屬于全人類,就算你死了,你還屬于這個宇宙。
比如你在學校和老師的關系很不好,老師成天數落你,同學們也在老師的帶動下笑話你——這等于是被自己特別在意的一個共同體排斥,這個感覺很不好。那么阿德勒的建議是在一個共同體中遇到困難的時候,你應該想想更大的共同體。
往大了看,你在這個小集體里的這點沖突,不過是茶杯里的風暴而已。當然也不是說就應該回避問題,但是首先你要想到,別的地方并沒有排斥你。
阿德勒這個“共同體感覺”的前提,是我們必須和別人建立橫向的關系,也就是人人平等。再進一步,你要把別人看作伙伴,而不是競爭對手。
其實絕大多數人和你并沒有競爭關系,沒人一天到晚盯著你較勁。現代陌生人社會中平等合作的關系其實是最簡單的。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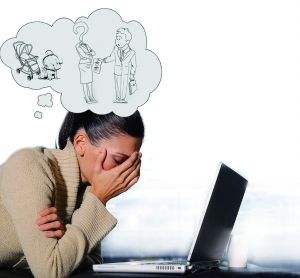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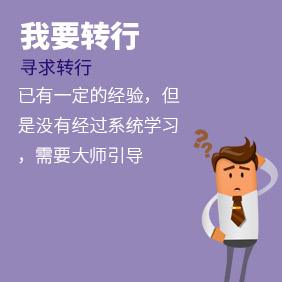


幸福不是由具體貢獻的大小決定的,而是由“貢獻感”決定的。這個很有感想